Giucy
組 長
 
UID 155267
精華
0
積分 14022
帖子 3412
閱讀權限 50
註冊 2010-2-24
來自 香港
|
【2012/03/18 信息時報】唱片死了,音乐会更自在地活着(提SHOW)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318/040211615531.shtml
盡管宋柯曾站出來反複強調,“唱片已死”是斷章取義,“音樂還活著”才是論述落腳點。但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就聯系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為在一般的概念中,唱片和音樂不僅是“皮毛”的關系,更幾乎是同義詞。但其實唱片業只是整個流行音樂產業的一部分,只是“唱片公司”的概念太過於深入人心,好像流行音樂只是存在於唱片或者廠牌里。但其實音樂介質的革命是世界性的,音樂消費模式的改變讓整個產業都在完成著新一輪的行業重組。而在看似羸弱的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無線音樂的年收入有300億,包括演唱會、卡拉OK等周邊產業,流行音樂產業至少有1000億的收入。就像原滾石唱片策略長張培仁所說:“現在的音樂更自由、更豐富、更多元、更有趣,比以前更可愛。”在唱片奄奄一息的末日,音樂似乎還有更自在的生存之道。
唱片之道:從音樂載體到身份證明
代表:五月天
在業內引起不小反響的台灣流行音樂紀錄片《聽時代在唱歌》中,相信音樂執行長陳勇志就認為唱片對於歌手幾乎只剩下身份證明這一個功能,即成為歌手和創作人的名片。而歌迷買唱片仿佛也就為得到一張會員卡,買到你就加入你認同的創作者或者偶像的創意組織,唱片公司要給歌迷的,是唱片之外更多的東西,包括MV、演唱會以及生活方式。而相信音樂和五月天最早想出“買專輯就唱校園”營銷策略,用買專輯送演唱會門票的方式,成功讓《后青春期的詩》專輯銷量在2008年突破20萬張,縱觀整個華語樂壇都已經算是奇跡。而2011年底的《第二人生》則分為“明日版”和“末日版”,供歌迷自由選擇,也再次讓實體銷售突破20萬張。
而作為中國內地最大的唱片發行公司,星外星唱片通過市場調研得出單純就唱片市場也依舊有其存在空間。獨立廠牌風和日麗創辦人卓煜琦就表示:“在數字音樂時代,降低了創作和宣傳的門檻,但相對的,在人人皆可發聲的年代,對於品質與創意的要求,就成了流行歌曲最被考驗的部分。網絡的壞處是,鼓勵大家都當創作者,卻沒有建立價值標准的機制,以前都是去錄音室錄音,現在只要有一台電腦就可以做電子音樂了,流行音樂美的標准就變得模糊。”而傳統唱片畢竟還有自身的一套審美標准,所以無論是高端的發燒唱片以及版本收藏,或者是低端的汽車音樂網絡音樂,唱片載體都還是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功能發生質變,甚至不再承擔商業價值。
歌手之道:獨立自主做老板
代表:周杰倫、張靚穎
產業發生變化,相應的歌手身份也發生改變。作為最成功的音樂公司——杰威爾的總經理楊峻榮表示:“當下的歌手已經不僅是在和同行藝人競爭,還要和電玩競爭,和手機競爭,和電影競爭。消費者選擇越來越多,同樣成功藝人的門檻要求就越來越高,歌手除了自己創作,還要跳舞,還要樂器,必須要有更多的條件。”主流唱片有既有的體制和觀念成了束縛,而為了更大的自主性,原阿爾法唱片老總楊峻榮就聯合周杰倫、方文山合組杰威爾:“藝人和創作人越來越重要,周杰倫的作曲,方文山的作詞,靠創意結合起來,上舞台讓大家評分。分立出來還是自由度的問題,我們可以自由地決定怎樣和消費者互換概念和感覺,而周杰倫的創意怎樣去滿足,都不需要經過太多的審核。”
杰威爾不是唱片公司,而是音樂制作公司,與此同時,獨立唱片和獨立制作開始興起,有創作能力的歌手們紛紛成立自己的公司。比如五月天聯合原滾石執行長陳勇志、張震嶽聯合原滾石營運長黃靜波,藝人與專業經理人成立自己的品牌,歌手也因此更能掌握自己的音樂事業,傳統唱片公司只剩下發行和銷售功能。五月天瑪莎就表示:“我希望我的歌曲就是我的招牌,不想因為有大唱片公司的政策或者方向的偏差而變成市場的犧牲品。自己決定音樂的宣傳和演唱會,自己去樹立自己的品牌。”而包括張惠妹、王力宏等同樣先后從唱片公司分離自組公司,這種歌手自立公司再與傳統唱片公司合作的模式很快延伸到中國內地,比如張靚穎唱片約簽給環球,而自己卻有少城時代作為經紀和音樂制作,后來更簽下楊冪。
盈利之道:演唱會成為拳頭產品
代表:張學友、王菲
唱片銷量無法盈利之后,演唱會成為最重要的音樂消費方式,陳勇志解釋說:“相信音樂抓的就是兩個東西,一個是演唱會制作,因為每一場演唱會都不能複制,而體驗行銷在虛擬世界里是非常需要的;另外一個就是創作歌手,因為只要創作者的精神和想法夠獨特,也是不能被複制的。”
陳勇志進一步解釋說:“當一個世界變得越來越虛擬的時候,面對面的很實在很實際的需求會相對變大。像現場演出這種每一場都會有不同,在心理因素上就會變得有價值。演唱會可能是這個時代的第八或者第九藝術,是這個時代的綜合藝術,是流行音樂新內容的最好的起點。”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相信音樂成為行內標志性的音樂制作公司,而五月天除了在台北小巨蛋連開7場創下紀錄,而北京鳥巢的演唱會十萬門票更是在三分鍾被秒殺搶光。
當下無論是偶像歌手還是實力派,無論是出道不久的新人還是久未露面的老將,幾乎全部都在巡演。所以張學友2011年唱過108場都不停歇,足跡開始向二三線城市滲透。有號召力的攻占體育場和體育館,名氣稍遜的二三線歌手有更為廣闊的城鄉結合部乃至大大小小的拼盤、慶典、年會、剪彩、酒吧。大牌諸如天后王菲唱酬外傳650萬,而張學友、周杰倫、陳奕迅、五月天、鄭秀文等均在四五百萬之巨。而諸如澳嘉娛樂旗下歌手歡子,“宇宙天團”鳳凰傳奇等,出場費雖不比巨星,但可以以量取勝,一場十萬、二十萬市場廣闊照樣收入不菲。而早前一直不直接參與演唱會制作的公司也紛紛重整旗鼓,滾石唱片運作的“滾石30”超大型演唱會更是延燒到“滾石31”,還會一直紀念下去。
合約之道:經紀約唱片約相互分離
代表:周杰倫、羅志祥
沿襲國外唱片業的傳統做法,華語唱片公司一般都不與歌手簽完全經紀約,而隨著唱片市場的蕭條,藝人經紀部分變得越來越重要,唱片公司的話語權就更顯式微,因而只能通過戰略合作的方式參與運作。再以周董為例,唱片的制作公司是杰威爾,發行則歸索尼唱片公司,“超時代”巡回演唱會的制作公司是台灣巨炮公司,演唱會硬件設備由瑞陽公司提供,演唱會經紀在不同地區又由不同公司負責。
一般演唱會的商業模式是,制作公司把演唱會賣給各地演出商,演出商通過票房、讚助等獲得收入。周董的內地經紀公司巨室音樂的經紀事務是向杰威爾收取10%的服務費,然后與各地“有關部門”以及演出商打交道,使得演出批文可以順利拿到、演出可以被賣給最適合的當地演出商、藝人的電視節目和代言等通告的價錢能夠相對公道。而在前幾年,周董巡演僅硬件設備的成本就已經高達1000萬元人民幣,還有高昂的場租費、人力成本、制作成本、宣傳成本等,只有巡演場次夠多,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攤薄成本。
而在藝人經紀方面,同樣也是戰略合作更多,前金牌大風華南區總監、現澳嘉娛樂董事總經理陳軻就表示,如果要全約簽下一個大牌歌手,高額的費用就很難承擔,並且風險巨大很難控制,除非你是陳家瑛這樣可以手握王菲和陳奕迅等大牌的超級經紀人。當下的許多唱片歌手往往有價無市,最有市場的是三類,一類是當紅偶像,如羅志祥、李宇春;一類是老實力派,如張學友;還有一類就是網絡歌手,如鳳凰傳奇。而包括唱片公司在內,大家通過戰略合作,各做擅長,共擔風險, 你擅長做經紀就做藝人經紀,擅長做演出就做演出制作,擅長做唱片就做唱片發行,大家坐下來分成,還是可以活得很好。而很多不能進入傳統大唱片體系的歌手,通過演出和代言照樣有可觀的收入。
表演之道:演電影演音樂劇多棲化
代表:李宇春、何韻詩
歌手轉去拍電視劇拍電影早已經不是新鮮事,包括周杰倫、王力宏等大牌歌手都已經過足導演癮,李宇春繼《十月圍城》后又在《龍門飛甲》過起3D癮。這其中的爭議也從未停止過,一方面歌手不務正業,注意力轉移之后勢必影響音樂創作力;另一方面“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無可厚非。有玩得好的就有玩得不好的,孫楠、景崗山等十余位內地音樂人出演的電影《盜版貓》惡評如潮;高曉松請來韓庚、吳尊出演自己導演的電影《大武生》也是淪為笑談。很多歌手削尖了腦袋想鑽進電影圈,不惜放棄音樂本位而只為混個臉熟,至今未有“觸電”的專職歌手已經屈指可數。
與紮堆影視的浮躁相比,音樂劇和舞台劇也正在成為一個突破口,越來越多演唱會的模式融入舞台劇元素,比如張信哲、何韻詩等人都已經開始嚐試,而音樂教父羅大佑也有龐大的音樂劇計划,台灣綜藝教父王偉忠則聯合音樂人陳建寧開始全新的音樂劇嚐試。
這是否意味著歌手離音樂本位越來越遠?原滾石策略長張培仁表示:“以前你可能通過各種的后制手段讓音樂變得光彩亮麗,消費者就上鉤了。現在他可能會回過頭來,去面對幾個基本問題,第一個是音樂本質做得到底好不好,音樂的感情有沒有做到位,第二個就是美學,你這個音樂出去的時候傳播的風格訊息鮮不鮮明,創意、視覺、影像、平面、美術,有沒有辦法把這個訊息適切傳達。”
當音樂的存在方式不斷擴展,華語音樂日漸稀缺的,卻是阿黛爾這樣能唱出心碎靈魂的“純粹的歌手”。要知道,雖然2011年度數字音樂收入首次超過傳統唱片音樂收入,但阿黛爾的唱片《21》實體銷售竟超過1800萬張。說到底,演唱會或電影再賺錢,華語音樂世界是否能孕育出自己的阿黛爾,才是流行音樂的真正希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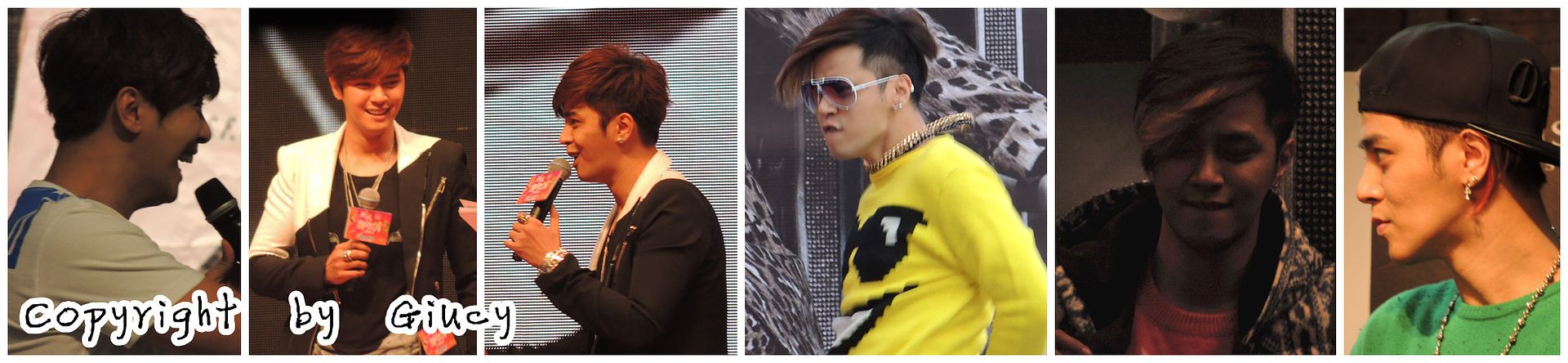 |
|



